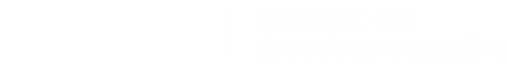他深耕哲学研究,是复旦大学外国哲学学科的奠基者;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俄等多门外语;他教书育人,以“手工作坊式”的精耕细作,悉心培育学生;他与书籍结缘,与夫人先后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他便是上海社科大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全增嘏。
12月5日下午,全增嘏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文科图书馆特藏中心举行,全增嘏先生纪念文献展在卿云书屋揭幕。全增嘏家属、弟子及后辈学者济济一堂,追忆大师精神风范。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哲学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图书馆共同主办,是复旦大学“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学贯中西,在复旦多领域遍洒星光
百年前,茫茫大海之上,一艘邮轮正缓缓驶向美国。梁实秋、陈植、顾毓琇、吴景超、吴文藻……乘坐此船赴美留学的青年学子,后来为我国思想文化界洒下了熠熠星光。
时年20岁的全增嘏也是这艘船的乘客。他出身书香门第,是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的后裔,13岁便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堂读书。赴美留学期间,全增嘏以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勤勉求知的态度,给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用两年时间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学位,三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并修完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课程。这名中国学生还担任过哈佛大学辩论队队长。
归国后,全增嘏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在《中国评论周报》和《天下月刊》上编辑和发表英文文章,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从上世纪40年代起,全增嘏任教于复旦外文系,担任系主任,直至50年代中期复旦筹建哲学系,转任哲学系教授。

全增嘏与夫人胡文淑
在外文系任教十余年,全增嘏对外国文学尤为关注,对狄更斯小说更是情有独钟。全增嘏的夫人是复旦中文系教授胡文淑,他们共同翻译的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堪称图书翻译的楷模佳作。该书是狄更斯小说中哲理最强也最难译的一本,夫妇二人常常为求一字一句的最佳翻译而争得不可开交。全增嘏还在《复旦学报》上发表论文《读迭更斯》,全面总结狄更斯的小说创作,融摄对十九世纪西方哲学的思考,学术性和思想性极高,至今仍不失为狄更斯小说研究的高质量文章。
全增嘏英文造诣很深,笔译、口译、中英文互译,样样精通。他还曾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等翻译了多本高难度的自然科学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以及《爱因斯坦论著选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等,其高超的英文水平、深厚的知识底蕴可见一斑。在全增嘏看来,专业英语能力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技能,因此亲自培训学生的专业英语。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刘放桐回忆,全增嘏曾专门为系里一些英文水平不佳的青年教师开设了“外语辅导班”,地点就在他家里。“他对这些青年人一句一句地耐心指导,手把手教学,没有哪位老先生像他这样用心了。”
在复旦,全增嘏不仅与外文、哲学结缘,还与图书馆结下深厚缘分。上世纪40年代,全增嘏担任复旦图书馆馆长,而夫人胡文淑刚好是前一任馆长。“大师伉俪接任馆长”,在复旦图书馆百年馆史历程中传为佳话。
融会贯通,拓荒深耕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父亲是一个求学者,他总是讲‘学海无涯’,一生孜孜不倦地做学问。”全增嘏的儿子胡庆沈记得小时候,每晚10点左右,准备入睡时,总是能够看到父亲的房间里,一盏不熄的灯,一个专注的身影,沉浸于阅读文献、编著教材、批阅文章……与满架古今中外书籍为伴。

西方哲学是全增嘏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洋哲学小史》,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不到五万字,却涵盖了从古代到现代(20世纪初)二千多年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化发展历程,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是一本专业性与普及性兼具的读物,是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
“精当,无水分,没废话。时至今日,谁要是记住了这不到五万字的‘小史’,他可以说是掌握了西方哲学的‘大要’。”复旦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黄颂杰曾撰文评价《西洋哲学小史》,认为此书凝结了导师全增嘏一生做学问、从事教学科研的特点: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时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全增嘏转到哲学系,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逻辑学教研室主任。 1961年初,全增嘏率先在复旦开设现代西方哲学的课程,当时全国高校“只此一家”,不仅奠定了复旦大学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中国现代西方哲学教学的先河。
70年代末,全增嘏带领复旦哲学系全体西方哲学教师,主编从古希腊至现当代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册)。该书打破以19世纪为界将西方哲学一刀两断的传统分期方法,整体观照西方哲学,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勾画了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史的全貌。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学习西方哲学史的主要参考书,先后重印15次,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在主持编撰《西方哲学史》期间,全先生就像是我们的‘大家长’。开会期间,他要言不烦,为我们提纲挈领、把好方向,让我们迅速投入到编撰教材的过程中。”复旦哲学学院教授张庆熊负责编写“分析哲学”部分章节,参考全增嘏等学者的相关论文,完成了初稿。“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不足之处,让我尽可能搜集外文的原典资料,仔细阅读钻研、重新打磨,这提高了我对于原始文献的重视。”
薪火相传,凝聚复旦哲学学科发展的力量
1962年,全增嘏开始正式招收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从那时起,复旦第一宿舍全增嘏家中的起居室,成为学生们的课堂。“父亲对待教书育人,可以说是尽心尽力。”胡庆沈当时还在读初中,总听见父亲和学生在家里讨论着高深的哲学问题,母亲则热情招待。有次胡文淑开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增嘏回应说:“就应该这样学才学得好嘛!”
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建立学位制度后的首批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位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全增嘏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坚力量。在西方哲学的专业学习上,全增嘏强调对古希腊哲学的重视,以及阅读经典原著的重要性。在治学态度上,全增嘏要求学生必须严谨、踏实,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当年就读于复旦哲学系的学生,很多都受到了全增嘏的言传身教。
“全先生学识渊博,为人谦逊,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学者、老师。”张庆熊回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复旦读研期间,尽管导师并非全增嘏,仍然受到了很多指导与教诲。“有一次我向老师请教‘无差别的爱’的概念,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打了你一耳光,你还把另一边脸转过去给他打。’他总是能把哲学的概念讲解得通俗易懂,让学生了然并牢记于心。”时过数十年,谈起与全增嘏相处的细节,张庆熊犹带笑意。“当时我没有电话,到老师家拜访,时常没有预约就径直前往。有一次老师正在洗脚,看到我‘贸然闯入’,脸上毫无愠怒之色,照常与我交谈。”
在学生、后辈眼中,全增嘏待人随和,对青年学生没有一点架子,关心备至。早在上世纪60年代,全增嘏家中就购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是当时国内少有的。一些系里的师生经常来到他家,排排坐好,观看电视节目,丰富文化生活。全增嘏通常在另一个房间照常办公,接待来访者,有时也与师生一同观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学明也曾到全增嘏家里看电视。他还难忘初出茅庐时,第一次翻译三、四千字的英文文章,没有信心,于是向全增嘏请教。“这位大学者逐字逐句地帮我校对翻译稿,耐心又细心,让我非常感动。”他认为,今天对全增嘏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复旦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好,达到顶尖水平。
尽管只见过一两次,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对全增嘏等“建系元老”的精神风度,始终感怀于心。“我入学复旦时,哲学系外国哲学的梯队很强,学科实力雄厚,而且各二级学科之间没有门户之见,互相交流促进。这与全先生那一辈老先生的表率作用,密切相关。这些优秀传统延续至今,使复旦哲学学科在国内名列前茅,对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不断推动哲学学院的发展。”
“我觉得不只是全先生一个人使西方哲学史学科和哲学系发展起来,而是以全先生等‘五老’为核心,有一种凝聚的力量。这种凝聚的力量,不仅只是学问的力量、学术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做人的力量,一种品格的力量。”复旦哲学系教授余源培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饮水思源,我们永远感恩和怀念全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他们永远活在哲学学院的骨子和精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