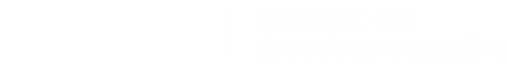陆谷孙(1940.3.3—2016.7.28):生于上海,籍贯浙江余姚。1965年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到访复旦大学时,曾到他的课堂上听课。1984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1994年被评为复旦文科三大“杰出教授”之一。1996至1999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系系主任,2003至2006年间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曾兼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亚洲辞书学会副会长,上海申博和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等。

主编《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著有《余墨集》《莎士比亚研究十讲》等,英译汉文字200万字左右,撰有《逾越时空的哈姆雷特》等论文40余篇。
编词典就像做厨子
在学术界,陆谷孙是公认的“英语大师”。提起先生的名字,人们总是能马上联想到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这部词典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影响难以估量。有一次语言学家陈原对陆谷孙说: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是的,陆谷孙开始也觉得枯燥。可是,编着编着就觉得有创造性了,“很有一种自我实现的乐趣、快感。”他说,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这埋头一做,就是40多年。
“偏向疏篱断处尽,亭亭常抱岁寒心。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这首诗道出了“陆老神仙”的风骨。
陆谷孙,这个名字随着《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的诞生而印刻在我们这个时代。


1991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是由中国学者独立编纂的第一部大型双语工具书,至今仍是同类词典中最具权威性、使用率最高的工具类图书,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它的主编正是陆谷孙。自本世纪初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陆谷孙又“与所剩无多的时间赛跑”,全身心投入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下简称“《中华汉英》”,上卷已出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但凡涉及中英互译的问题,我最先想到的、麻烦最多的,就是陆谷孙先生。在微信上、在电话里,或者说在我心中,他给出的回答一定是中英互译的最佳版本。他总是飞快而耐心,却又那样审慎,常常挂了电话不一会儿,微信上又冒出他认为更精妙的译法。
但陆谷孙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编一部既能查到“灰天鹅”又能搜到“学渣”的汉英词典
在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以陆谷孙的才学,若是编教材、外出授课,哪个收益不比编词典高?但他坚持要做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而且做了40多年。编词典从来都不是轻松的,常常要“用理想主义的血肉之躯撞击现实的铜墙铁壁”(陆谷孙微博签名档)。在1991年编完《英汉大词典》之前,陆谷孙就对自己提出 “三不”——“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写书”。这部词典的编写队伍,1970年初编时有“108将”,到了1986年仅剩下17个人,被任命为主编的陆谷孙硬是带着“老弱病残”又花了四五年,编完了这部至今被认为是中国人学英语最好用的词典。
按陆谷孙五年前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言,未竟的 《中华汉英》是他“最后的事业”,是一件让他“牵挂了20多年的事”。1991年刚编完《英汉大词典》时,他在香港遇到从事对外汉语工作的安子介,安子介对他说,林语堂、梁实秋他们英汉、汉英词典都编过,你为什么不再编本汉英词典?于是,“被勾起了虚荣心”的他,从1990年代末开始着手这一工作。
《中华汉英》的编纂流程是由编者提交初稿,而后由主要编写人员修订,再由执行主编修订,最后由主编陆谷孙审定。“陆老师自称‘老改犯’,他的校样看起来像是打翻了墨水瓶,常常为了一个词条一遍遍地修改,或是调整翻译用词,或是重新选择例句。”《中华汉英》责任编辑于文雍记得,陆先生说过,编词典过程中“改”是没有止境的。但“如果没有无休止的改和加,《新英汉词典》能累计售出一千万册吗?”
陆谷孙自己 “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甚至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符合最广大读者的需求”。他有着丰富且庞大的阅读量,关心时事,且非常喜欢随手写——伸手可及的信封、明信片、小纸片上常常写满他的最近收获。
陆谷孙门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高永伟说,陆先生一直特别关注收录新词。1990年代跟着先生编纂 《英汉大词典补编》时,先生就叮嘱他,每天要在最新的报纸、杂志中找新词、热词。但编词典时不能照单全收,比如入选的词必须在不同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过至少3次,而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
在高永伟看来,《中华汉英》就有着浓重的“陆氏风格”。翻看《中华汉英》上卷,最近几年流行的许多汉语新词、热词扑面而来。其中既有高大上的专业词——灰天鹅(grey swan)、标签云(tag cloud)、光保真 (light fidelity,Li-Fi)、可穿戴设备(wearable device),又有挂在嘴边的时髦话——高级黑(last word in being negative)、草根(grass-roots)、海选(mass election),等等。占比较大的是与计算机、手机和网络相关的词汇,正如陆先生所言:“今天编词典要着重顾及使用者的大头——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双机人’:计算机和手机用户。”比如 低 头 族(phubbers)、建 群(to set up a group[in netspeak])、点 赞(to push the“like”button;to give the thumbs up)、给 力(boosting;stimulating;cool;awesome)、爆 表(to go beyond index;to exceed the upper limit)、呆 萌(silly and cute;adorably foolish;adorkable),等等。
“陆老师一直要求我们多看英文书籍、报刊、杂志,然后反哺到汉语翻译中,这样译文就有了地道性。”高永伟说,除了记录下汉语新词,陆先生还想方设法在词条或例证的译名中,体现英语新词的用法。例如,在“矫情”表示“pretentious”的义项下,设置的例证是“当地铁上其他人都在低头玩手机时,正儿八经地看书难免会觉得有几分矫情(when all else is phubbing on the tube,reading a serious book may seem somewhat pretentious)”,其中所用的“phubbing”一词2012年才首现于澳洲报纸。
对于一些成语、俗语、谚语等,陆先生尽量用英语中地道的习语来对应翻译,尽最大可能实现词目和例证的 “等值翻译”(陆谷孙语)。例如,对“进退维谷”除了提供最为常见的 “in a dilemma”之外,他还提供了两个英语习语——“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和“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把汉语、英语中最优美的部分通过词典这个窗口展示出来”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院训,是陆谷孙早年提出的:“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强调的是知识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据说他最担心外语系的学生中文不过关,“中文都没读好,怎么读得好英文呢?”
陆谷孙曾提出,《中华汉英》的一部分受众是国人,他希望可以让不熟悉古字、古词和舶来专业术语的年轻读者,通过名言、熟语、谚语、歇后语等汉语词条所对应的英语解释,提升对本族语的认知,补一补传统文化的课。同时,他更希望能让对中华文明感兴趣、想学汉语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与文化。
据统计,《中华汉英》的百科类属标注中标注“Chin(中国的)”的中国特有词汇有504个,“Chin Med(中医/药)”的有734个,“Chin Myth(中国神话)”的有227个。而且,词典里还有大量摘自中国经典名著的警句、箴言、妙语等,有些还用☆加以标注。比如,在“合”字头下,加有此标注的例证多达6条,分别摘自《庄子》 《孙子兵法》 《周易》《战国策》及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
在词典中,还有不少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是通过字面直译加注解的方式来翻译的,以帮助外国人理解。比如 “闭门羹”[(stew prepared for a brothel client but admittance refused) no admittance;refusal of entrance;door slammed in one’s face;cold-shoulder reception]、“斗地主”(fight-the-landlord[3-or 4-party card game to outplay the side passing for a rural landlord]),等等。
另外,《中华汉英》里还收录了港澳台地区的典型用语近1000条,以及汉语各大方言区中的常用词语,如 “忽悠”、 “刮三”等,“使其成为汉语里面一个共核部分,借助英文翻译让大家培养认同感,何乐而不为?”(陆谷孙语)
于文雍介绍, 《中华汉英》收录了大量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习俗等有关的词汇。在业已出版的上册中,仅成语就逾2万条。此外,不乏古汉语条目,甚至象形文字,这在同类型同体量的汉英词典中是一个突破。“从无到有是最难的,陆先生就愿意做这件难事。”更难的是,陆先生“提供的例句或文采斐然,或风趣幽默,还能引发人们思考”,他希望“把汉语、英语中最优美的部分通过词典这个窗口展示出来”。“从《中华汉英》就可以看出来,陆老师为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费了多少心。”
说起陆谷孙的这份情结,不能不提他的父亲陆达成。陆谷孙曾说:“俗世给了我很多虚荣,但我最看重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曾翻译过法语书的陆达成,要陆谷孙从小读的是《朱子家训》《曾文正公家书》等中文经典。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陆谷孙当外文系主任时,会开设“白菜与国王”系列讲座,请余秋雨讲文化、冯亦代讲新闻、董鼎山董乐山兄弟讲翻译、陈钢讲《梁祝》作曲、黄蜀芹讲电影、俞丽拿拉小提琴。
陆谷孙戏称自己是 “假孤老”,他的太太、女儿早就移居海外,且早已有第三代,但他只是隔年去与他们团聚。至于他自己为什么坚持留在国内,他曾引用两句话作答。一句是捷克作家克里玛说的“我没有参与创造国外的自由生活,因此我并不留恋。我的心还在布拉格。”一句是杨绛说的“我们都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或许于文雍的解释更直白一些,“陆老师认为,他在国内的作用更大”。
以前外文学院新生入学时,会请陆谷孙给大家上入学教育第一课。他曾说:“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心中有这条道德底线,不要欺骗、钻营、庸俗、猥琐,而要用一颗忠诚、明敏的心,保持对问题的省思与追问。”很多人觉得,这就像陆谷孙一生的写照。
“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
陆谷孙曾说,他喜欢孤独、不喜交际应酬,“还是老老实实当我的教书匠为好”。许多学生在上过陆谷孙的课后都说,听他上课是一种享受。尤其他讲课时的“陆氏幽默”。按他自己的要求是“一堂课,起码要让学生笑3次”。除了本院学生,复旦其他院系甚至许多校外的人都会赶来听课,以致有时教室中座无虚席,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复旦大学听课,讲课者即是陆谷孙。
2015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曾召开过一次隆重的聚会,纪念陆谷孙先生执教50周年。陆谷孙读研究生二年级时,因外文系缺教师,他就被安排教大五的毕业生。为了不丢面子,他总是“精细地备课”——把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背出来,然后对着镜子练。负荷最强的时候,他每周要上14到16节课,每晚还有2个学生要找他练口语,同时还得完成自己的研究生论文。那次纪念会现场来了几位陆谷孙最早的学生,他们一起唱了几首歌,都是陆谷孙当时为了让大家学好英语自编歌词的“原创歌曲”。
陆谷孙是莎翁研究专家,1982年时他即凭借《逾越时空的哈姆雷特》一文,成为第一位在国际莎学讲坛上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他在课堂上教授的一些莎士比亚名篇,让很多学生因此走近了被认为极其深奥的莎翁。

《英美散文》这门课,陆谷孙一直坚持讲授到2014年,当时74岁高龄的他因腔梗住院后不得不停止教学。陆谷孙弟子、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谈峥至今记得,1987、1988年间他读大四时,陆老师给他们上 《英美散文》课的情景。“陆老师上课时,声音在教学楼走廊里好远就能听见。这说明他上课是很用力的。”
在1997年春心脏早搏发作最严重的那段日子里,陆谷孙仍然坚持抱病上课。甚至在学生发现他脸色苍白,体力不支,好像透不过气来,要立刻送他去医院时,他还是坚持把课上完。下课后,他就被直接送往新华医院抢救。成群的学生捧着鲜花去医院守护、看望他。
“陆老师在教学上一直在动脑筋。”谈峥说,陆谷孙曾告诉他,自己上了几十年的课,但有时上课前一晚还会兴奋得睡不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师,在上课之前,还因为要面对学生而兴奋得睡不着,这种精神实在是很难得的。”
陆谷孙常说:“学术是我生命的延续,学生是我子女的延续。”自1965年从教以来,陆谷孙即使担任行政、科研工作,也承担了大学英语教学和英语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工作量远远超过了学校的规定。2000年他跨入了60岁的门槛,但教学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本科生开设的基础课达400课时以上,给研究生上课350课时以上。
陆谷孙批阅过的学生论文,哪怕是厚厚的一叠,他也都一字一句地批改。在一些他认为“低级错误”的地方,他会画上标志性的“大眼睛”作为警示。批阅到最后,他还要写下一长段评语,据说是为了“让每个同学觉得自己是受重视的”。
平时,只要是学生去找陆谷孙讨论问题,不管认不认识,他都热情接待,帮忙查找资料,而且毫不犹豫地借书给他们。不管是不是他门下的学生,他都提携奖掖。许多复旦的本科生、研究生,都在升学、留学、求职、文章发表等方面得到过他的帮助。
陆谷孙还一直从自己有限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贫困学生和有困难的同事、朋友。仅是他经由弟子们之手散出去周济贫困学生和院系职工的钱,就数以十万计。
尽管获奖无数,但在陆谷孙的家里,几乎看不到奖状、证书。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在复旦以第一高的票数当选“本科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他说那是“给我喜悦最多,让我最感动的一次”。